第一次接触飞盘,是体育课的活动。老师让我们分组,我负责传球。飞盘落在我手心的那一刻,比同学们的笑声还要清脆。我紧张地抬起头,眼神穿过场地的柱子,看到同学们的眼神里有期待。我并没有特别强的手感,但当指尖触到圆圆的边缘,空气中的味道就变得不同——像是清晨的露水,带着一点金属的清脆。
我知道,我愿意试着追逐这种感觉,哪怕跌倒、受挫,也要把它变成前进的动力。
采访人:你为什么愿意坚持下去?赵芳:因为飞盘教会我一个简单的道理:过程的美在于持续,而不是一瞬的高光。每一次起跳、每一次接断,都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。训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表演,而是一支队伍的协作。那时的我,身体条件并不出众,反应也慢半拍,但我相信只要日复一日地练习,线条会变得顺滑,判断会变得更果断。
校园的日子像一场被不断重播的练习课,我学会在喧嚣中保持安静,在忙碌里不失耐心。
采访人:能不能给正在起步的年轻人一些具体的感受?赵芳:第一,耐心。技巧不可能一蹴而就,尤其是传球的准心和跑动的细节,需要海量次序的重复。第二,观察。看对手的站位,读队友的体态,把每一次攻守转换视作一个故事的转折。第三,关心团队。飞盘是没有裁判的,每个人都在场上讲述自己的记忆,信任是最好的传送门。
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成名,可我已经懂得把时间变成盟友,把每一个练习日都当作投资,累积属于自己的价值。
采访人:第一次省级比赛的记忆呢?赵芳:那是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感觉。我们在风口上打拼,队友之间的目光像无声的契约。记得在关键时刻,我接到队友的横向传球,身体像自带弹簧一样跃起,手指轻轻一抛,飞盘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穿过对手的防线,最终落在了我的目标区域。
比分翻红,观众席的欢呼像浪潮,一下又一下冲击我的心跳。我才明白,所谓天赋,很多时候只是把练习日复一日地变成肌肉的记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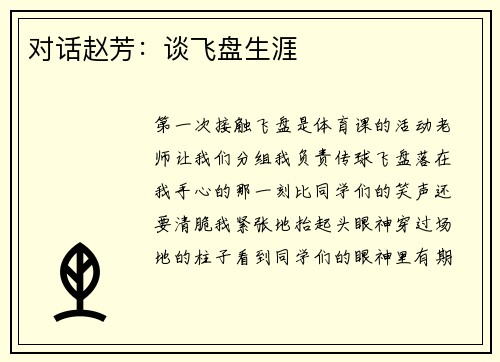
采访人:在你的成长里,哪一刻最让你心疼?赵芳:挫折永远不会缺席。一次训练中我因为一次错误的传球让队伍失分,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,担心被斥责、担心自己拖累了队友。教练没有责备,反而在第二天的训练里用一个简短的演示点醒我:每一个错误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。
VSport官网自那以后,我开始用日记记录每一次训练中的选择,学会在错误里找方向,而不是让错误定义自己。飞盘的语言里,失败只是一个分支,真正的目标是让自己站在风口还能保持冷静。
采访人:进入成年阶段后,你的职业轨迹是怎样的?赵芳:成年阶段,我把训练的强度和战术理解提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加入省队后,我们把日程设计得更像职业队:晨练、技术练习、对抗训练、战术录像、康复与休息的平衡。真正改变的是对比赛的理解:场上不是个人炫技的舞台,而是策略与信任的博弈。
我们在国内赛事中逐渐站稳脚跟,甚至有机会代表国家队出征世界赛。每一次出场,我都提醒自己:别让情绪支配判断,保持专注,照着既定的计划执行。
采访人:有哪些难忘的高光时刻?赵芳:有。代表国家队出征世界杯时,我们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分钟落后。队友通过默契传球,我们完成了一个连续的短传配合,完成反超。观众席全场起立,那一刻我意识到努力没有白费。另一件事是教练和队友在休赛期的支持。我们没有豪华的设备,只有彼此的信任和持续的训练。
每一次训练结束后,教练会给每个人写下进步点和目标,这种细致的关注让我感到被看见。
采访人:你也经历过伤病,对此你如何调整心态?赵芳:伤病像一场悄无声息的风暴,来得突兀也来得慢。最初的两个月几乎成了观众,我无法在场上发力,心里很急。后来我学会把注意力放在康复的每一个小步骤上:拉伸、肌肉平衡、姿态矫正。治疗的我开始研究比赛录像,分析对手的战术,确保一旦回归,能以更清晰的思路参与竞争。
康复不是弱点的承认,而是对自我负责的一种表达。逐渐,我的体能回升,跑动变得更灵活,传球也更加精准。
采访人:你对未来的飞盘生涯有怎样的规划?赵芳:愿景是把技术和领导力结合起来。作为队内老将,我愿意把经验传授给年轻人,帮助他们建立自信、掌握节奏、理解比赛的节奏感。未来的赛季,我希望把阶段目标拆成更小的里程碑:提升持续性、增强防守覆盖、在复杂局面中维持冷静。
更重要的是,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更多热爱飞盘的年轻人,让他们知道:坚持是一种自由,团队是一种力量,飞盘是一门关于选择的语言。
采访人:用一句话给正在追梦的读者。赵芳:别让恐惧阻挡你试错的勇气,把每一个练习日都写进记忆,把每一次落地都当作起点,走好属于自己的弧线。